
街头游戏厅,是8090一代人的童年印记,昏暗闷热的房间里闪亮的荧屏,是少年的欲望之火。有人在游戏厅里豪掷零花钱,有人在这里联机对战,还有人被父母抓包拎着耳朵回家,本文的作者不一样,10岁的他在人头涌动的游戏厅里,发现了商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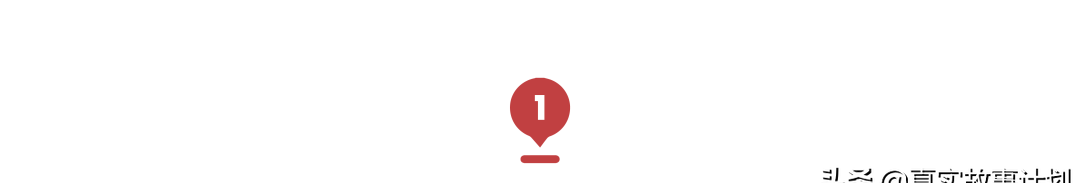
湖南衡阳湖北路上,有一家电子街机游戏厅,叫新世界。掀开皮质门帘,感官将受到冲击。这里弥漫着二手烟,噪音刺耳,霓虹乱目,六十台最新香港货从一楼蔓延到昏暗的地下室。
2005年,我刚上五年级,当我还在坦克大战上浪费游戏币时,同桌阿奎已经能一币通关三国志。
“你这也太无聊了,浪费钱。”阿奎不屑地瞥了眼我屏幕上的GAME OVER。
那天下午,我俩从三国志到恐龙快打,再到银河恶魔城,没有一个游戏我能存活超过三分钟。为了和好兄弟一起战斗,我只好用游戏币硬顶。
“没币复活了。”差一点就撑到关底了,我有些沮丧。
“等我通了这版。”阿奎轻巧地搓动摇杆,右手中指和食指快速敲打着按钮。扳倒了大Boss后,屏幕上绽放着像素烟花,浮现三个大写字母WIN,这在我的屏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“走,去搞点币来。”阿奎起身,才发现我们被目瞪口呆的小学生包围。“看屁啊,换币不?”阿奎挤出人群,口里嚷嚷着让小屁孩们散开,其实在炫耀他能搞到币。
新世界的规则很简单,年龄、性别不限,欢迎任何人前来凑热闹,但要想消费,必须年满十八。这是老板在这条街上做生意的规矩。出于对街坊邻居下一代的关爱,他时不时像赶苍蝇似的,催促东看西转的孩子回家吃饭。
趁老板不注意,小孩子钻到机台下面扒拉地板,寻觅别人落下的币。我和阿奎用不着这么费劲,阿奎的成年表哥天天泡在游戏厅,经他之手,我们的零花钱顺利变成新世界的营业额。
阿奎有稳定货源,吸引了其他小学生,他们不再冒着钱币两空的风险,去找吸烟烫头、刘海遮住一只眼的杀马特青年帮忙换币。
周六补习班课间,小客户们到教室最后一排,把零花钱、早餐钱交到阿奎手里,我负责用英文四线本登记班级、名字和金额。上课铃响起,还没交上钱的人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我和阿奎要花一整节课,把课桌膛里那些五毛、一元、两元纸币叠好,装进阿奎的牛津布书包。
上午课程结束后,我们会买上五毛一包的辣条,一边吃一边前往新世界,在老虎机前找到阿奎表哥。再要两瓶汽水,替表哥守着老虎机,等着那一袋银光闪闪的游戏币。
在游戏厅闲逛的青年,看到小孩子手上有币,会说:“小鬼,借几个币,明天还你。”为了避免被“有借无还”或老板一锅端没收,拿到币后,我们先各自回家,草草吃过午饭,再去学校后山的羽毛球场碰头。
早在沙坑旁等着的小客户们,三五成群,靠在爬梯上闲聊或者做游戏。见我们来了,所有的交谈和娱乐都会立马停下。十几双眼睛里闪烁着期待,那是我和阿奎的高光时刻。
在大樟树的树荫下,我翻开四线本,大声念名字和金额。阿奎清点好游戏币数量,放到面前的手心里。偶尔来了新面孔,我们温馨提示“不要把币一次性都带去游戏厅”。名单里总有一两个遭爸妈禁足,或在路上玩过了头的顾客,大部分人散去后,我们会再等上半个点。
十块钱换来20个币,我们通常留下2个。等四线本上的名字全部划掉后,还剩三四十个币,加上攒了一星期的零花钱,够我俩在游戏厅过一个愉快的周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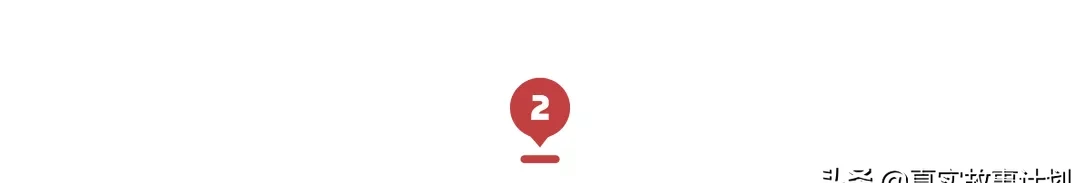
我和阿奎几乎垄断了湖北路补习班的换币业务。回想我们的创业契机,多亏了一枚游戏币。
四年级暑假,我乘上前往补习班的11路公交,投了一块钱,找位置坐下。下车后,我摸了摸口袋,来回两块钱路费一个子没少。原来刚刚被我投进收费箱的,是之前玩剩下的游戏币。我看着公交车扬长而去,生怕司机掉头找我要钱。
奥数课上,我神秘兮兮地伏在课桌上,告诉阿奎我的省钱小窍门。阿奎听了直拍大腿,差点引来老师,他压低声音:“有搞头!”放学后,我们每人找表哥换了20个币,五天路费一下子变十天,省下的钱能买好几包辣条。
我俩尝到了甜头,忍不住到处炫耀,一面让听众“不要告诉别人”,一面自己告诉下一个人。小伙伴听了都来拜托我们换“车费”。新世界的游戏币,一时间成了补习班地下市场的硬通货。
一开始,我俩是免费跑腿,既收获了信任,还能偶尔借个作业抄一抄。后来,大家换来的币用不完,还没等到投进公交车收费箱,就还给了游戏厅。街机游戏对小孩的吸引力,催生了我们的九折代购业务。
开学后的每个周末,我和阿奎都在补习班和新世界度过。其实游戏机玩久了,我有些腻了。可我俩从小厮混在一起,家离得近,每天约着上下学。阿奎喜欢玩,我便继续跟着玩。
阿奎喜欢玩对抗性强的拳皇、街霸,在新世界,没有人能在阿奎跟前挺过两个回合。来找他切磋的人越来越多,这小子泡在游戏厅的时间更久了。每周一次游戏币代购业务,已经满足不了阿奎。
站在新世界玩家顶点的小学生阿奎,在好胜心的驱使下,决定扩大客户群体。
在放学路上,他问我“要不要把生意搞到学校去”。我从小谨慎,万一惹来班主任和风纪校长,后果严重。但念及兄弟情谊和管账本的快乐,我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一节体育课上,我和阿奎猫在主席台后面,给隔壁班一起补习的老客户放出口风,叮嘱“不要张扬,最好找去过游戏厅的来光顾”。很快,其他班老顾客收到了消息。在信息课、自然课上,只要是能光明正大讲小话的地方,都有人在为我们宣传。
课间,时不时有几个学生到我们班后门探脑袋,在其中一人的指点下,看向我和阿奎。阿奎见猎狂喜,我也有一种当上风云人物的得意。我俩交换了一下眼神,可担心被班上的小喇叭告状,并不敢轻举妄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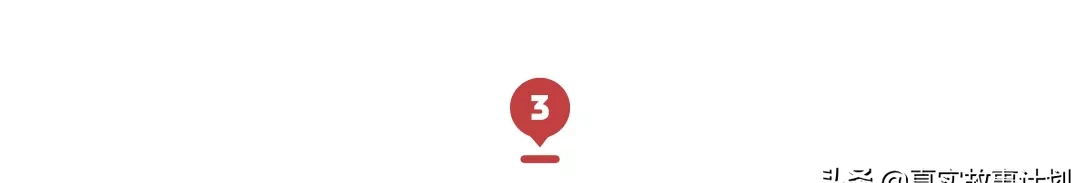
我们将第一次交易时间定在周五大扫除后。班主任站在讲台上,嘱咐我们“打扫好卫生早点回家”,便挎起小包下楼。我和阿奎拎着垃圾筐紧跟上,看着班主任走过喷泉、食堂、篮球场和荣誉墙,在停车场找到自己的电瓶车,骑出校门。电动门缓缓关闭,我和阿奎相视一笑,飞快跑回教室,静候生意上门。
校大道上背着书包的学生越来越少,我们教室里的学生却越来越多。收钱、登记、收钱、登记,放钱的书包拉链越拉越开。负责监督卫生的劳动委员见状,也乖乖交出攒了几天的零花钱。我们悄悄跟他承诺“游戏币给他时,一个子儿也不会少”,作为交换条件,我俩不用打扫卫生。
桂花树的影子从喷泉爬到了窗前,五点的放学铃也赶不走我们。为了不错过任何一笔生意,我和阿奎屁股不挪窝,边写作业边等着下一位顾客。
六点,我们等来了最后一位顾客,隔壁班的富二代小胖子。他斜跨着单肩包,用屁股顶开前门,双手各拿一袋炸鸡柳,边倒退边朝着我们喊:“还没走啊,还好没走。”
胖子来到我们跟前,放下鸡柳,从牛仔裤后袋抓出一把钞票,紫色和灰色中夹着红色。“帮我换,帮我换。”他放下钞票,用签子插起一块鸡柳,送进嘴里。
我点了点,三百七十四块钱,告诉阿奎,问他“怎么办?”阿奎书包里,原本估计也就三百来块,还是一块的居多。
“六百七十三个币,明天下午一点后山沙坑来拿,胖子。”阿奎的声音颤动着。
“好贵啊,没算错吧。”胖子说话的时候,嘴里的食物残渣飞出来。
阿奎拿起本子和笔,当着面算给他看。胖子压根看不明白,我补了一句:“你买这么多我们还给你优惠了,以后还有优惠。”
“好吧好吧,刚回去拿的钱,累死了,就这样吧。”胖子站起来,“再给我留四块钱打摩的回去吧,这个鸡柳请你们吃了。”阿奎果断抽出四块钱递给他。
胖子走后,我和阿奎激动坏了。这次没有白等,等来了金主。我们立刻收拾好书包,抄起胖子留下的鸡柳,蹦跶着离开了教室。出了校门,我们发现手里的鸡柳是十块钱分量,感叹这个朋友值得一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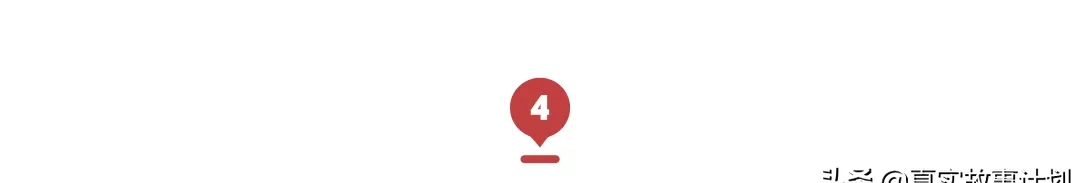
身上背着一笔巨款和写完的作业,我和阿奎的心情有些飘飘然。我们吃着鸡柳,聊起七点档的动画片,决定抄小路回家,能节省十几分钟。
那是一条不常走的路,穿过一片老旧居民区,再经过一个顶上跑火车的涵洞,非常无聊。如果走大路,可以看车水马龙、店铺百态,还会经过废弃的建筑工地和一座大天桥。一般不急着回家的话,我们会沿着大路走走停停,来榨干回家前的欢乐时光。
我们出了居民区,刚要进涵洞时,三个比我们高的男生迎面走了过来。我们忽略了一件事,六点半了,初中生放学了。看样子他们早就分好了工。红衣服的矮个子走过来,从后面抓住我俩的书包肩带;黑衣服的胖子拎着个塑料袋,站在巷子尾望风;瘦子叼着烟,直截了当地说:“借点钱用吧。”
我第一次遇到抢劫,张着嘴巴,不敢说话。阿奎面露难色,说:“我没钱了。”
“是吗?要是搜出来怎么办?”瘦子甩了甩刘海,吸了一口烟。
“真没了,都买东西吃了。”阿奎指了指我手里的鸡柳。
我反应迅速,双手一拱:“只有这个了,要吗?”
瘦子没搭理我,让矮子“搜一下”。矮子把我们衣裤口袋掏了一遍,又细心检查了校牌夹层,最后让我脱掉鞋子袜子,见阿奎穿的凉鞋才作罢。就在我以为他们要放人时,矮子说:“书包打开。”
我打开书包,他翻了个底朝天,发现一毛钱没有,好心把翻出来的书塞回去,骂了句脏话,踢了我一脚。
他的下一个目标是阿奎。阿奎牢牢抓住书包,矮子一边扯,一边对瘦子说:“这人不是之前遇到过吗?上次就搜出东西了。”
“还不放手呢?”瘦子把烟取下来,烟头对着阿奎的手。阿奎怕被烫,乖乖松了手。
阿奎的书包里,是我们全部的业务款。矮子惊呼:“草,你就这样放钱啊?”接着是两记清脆的耳光,打的是阿奎。
“你他妈说没钱?”瘦子面带喜色,“你要早拿出点钱来,我都放你们走了,非逼我们动手是吧,可以,动手费1000块。”
矮子补充道:“明天下午来这里,把剩下的补齐,晓得了不?”说完又踹了阿奎一脚,阿奎倒退了好几步,凉鞋搭扣都断了。突如其来的暴力让我不知所措,双腿不停发抖,脸也在发烫。
瘦子把钱装进钱包,感叹“小学生真尼玛有钱”,威胁道:“这事不准说出去,刚看了校牌的,你们跑不掉。”他喊了一声,黑衣服胖子急忙跑过来,拿走了我手里的鸡柳。劫匪消失了,我手心全是汗,腿还在抖,阿奎靠着墙,脸色煞白。
我俩捡起书包,一言不发地走进黑乎乎的涵洞。一辆火车经过,洞内吵得很,地面跟着抖动起来,我莫名其妙喊了一句:“你不是第一次被打劫啊?”阿奎张开嘴,在前方洞口亮光的照射下,露出了洁白的牙,他哭了。
我赶紧闭嘴,发誓下次遇见他们,一定狠狠地干一架。到家后,我没有胃口吃饭,倒在床上,想起瘦子的恐吓,还是没忍住掉了眼泪。
我和阿奎的合伙生意宣告破产。散客们和胖子反而安慰我和阿奎“不要紧”。胖子是过来人,挨抢专业户。而卑鄙的劳动委员,就为了他的十块钱,向老师检举了我和阿奎。老师请来家长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,放学带着我们转悠了两天,也没找到那三个劫匪,最后不了了之。
我们的小学时代,在下一个夏天结束了。新世界在2008年冰灾后歇业装修,再开门变成了牌馆,而网吧代替游戏厅,占领了湖北路的高地。阿奎在表哥的带领下,一头扎进了黑网吧。他告别了电子拳击,研究起散打和跆拳道,最终暴力统治了中专。
